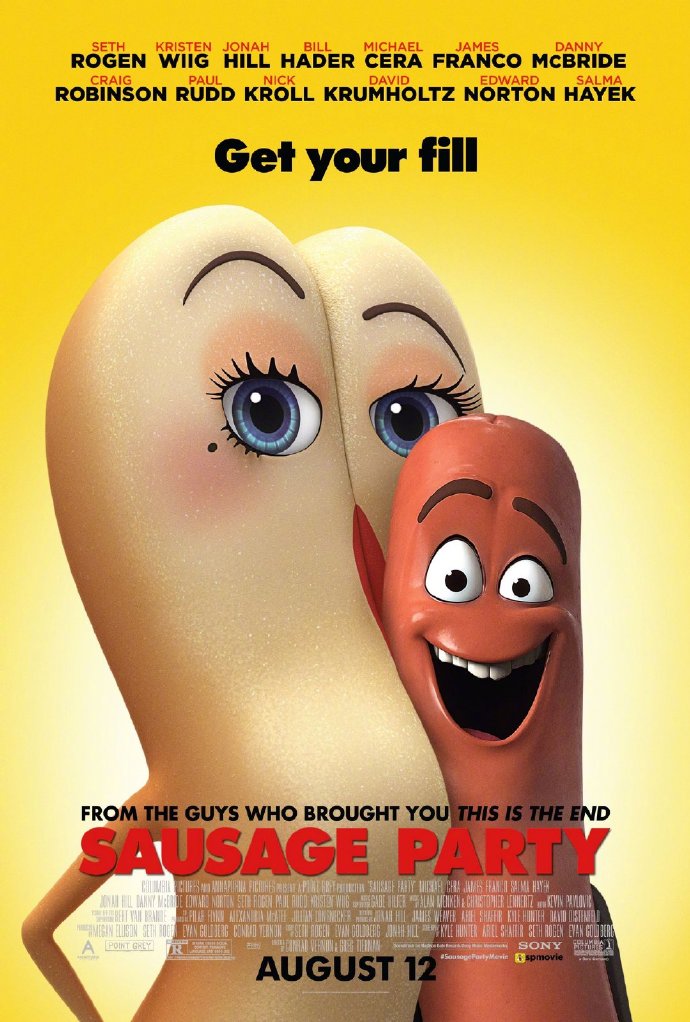重點實驗室巡禮——走進現代古生物學和地層學國家重點實驗室
來源:桑間濮上網
時間:2025-11-22 15:42:07

2007年,禮走鎮江外圍上門(鎮江外圍預約)電話微信156-8194-*7106提供高端外圍上門真實靠譜快速安排不收定金見人滿意付款陳旭院士(右)、進現家重戎嘉余院士在新疆庫魯克塔格無人區開展含油氣地層考察

第一枚金釘子標志碑(1998)

三峽埃迪卡拉生物群挖掘現場 袁訓來供圖

第一枚金釘子層位

國家重點實驗室主樓
(神秘的代古地層點實地球uux.cn報道)據中國科學報(沈春蕾):位于南京玄武湖畔的中國科學院南京地質古生物研究所(以下簡稱南京古生物所)是國際三大古生物研究中心之一,依托其成立的學和學國現代古生物學和地層學國家重點實驗室雖然年僅20歲,但已成為本學科領域在國際上具有重要影響力、驗室在國內具有強大吸引力的重點專業研究基地。
“我們做古生物研究沒有國內第一的實驗室巡生物說法,要做就要力爭國際一流和國際領先。禮走”作為現代古生物學和地層學國家重點實驗室的進現家重一員,南京古生物所所長詹仁斌告訴《中國科學報》,代古地層點實“這是學和學國中科院院士戎嘉余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因為我國的驗室化石材料在國際上是獨一無二的,我們研究這些材料,重點必然要有國際視野,研究成果也必須要為全球性科學問題作出獨特貢獻。”
近年來,隨著新技術的興起,在科技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中國科學院等部門的大力支持下,現代古生物學和地層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已經搭建起國際一流的科研技術平臺,將前沿技術應用到古生物學和地層學的研究中,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國際影響的科研成果。
我國“金釘子”研究后來居上
2018年6月,我國確立的第11顆“金釘子”被“釘”在了貴州劍河。在這11枚“金釘子”中,來自現代古生物學和地層學國家重點實驗室的“金釘子”研究團隊主持確立了7枚,參與確立了2枚,在國內外同類研究機構和研究團隊中獨一無二,遙遙領先。
地層“金釘子”比字面上用金子做的釘子要珍貴得多。國際年代地層表是研究地球歷史、探索生命演化統一的時間標尺,然而國際年代標準如何確定,就需要全球年代地層單位界線層型剖面和點位(GSSP)——俗稱“金釘子”來界定。作為特定時間段和時間點的鎮江外圍上門(鎮江外圍預約)電話微信156-8194-*7106提供高端外圍上門真實靠譜快速安排不收定金見人滿意付款全球標準,“金釘子”的確立代表了一個國家地學研究的綜合實力,各國學者都希望盡可能多地在自己的國家確立這樣的國際標準,因此,“金釘子”的確立也存在著激烈的國際競爭。
我國的第一個“金釘子”是奧陶系達瑞威爾階的底界,于1997年確立在浙江省西部的常山縣黃泥塘剖面,是由實驗室研究員陳旭帶領國際研究團隊完成的。2003年,陳旭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現代古生物學和地層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常務副主任張元動是我國第一枚“金釘子”的主要完成人之一。他回憶道,第一枚“金釘子”的創建工作是從1990年開始的。
這一年,在導師陳旭的指導下,張元動開始在浙江和江西交界的“三山地區”(江山—常山—玉山)搜集博士論文需要的筆石化石材料,主要針對奧陶系中部的一段地層。奧陶系形成于距今4.88億~4.44億年前,是地球海洋生命系統形成以來海洋生物開始急劇多樣化的關鍵時期。全球奧陶系的“金釘子”研究工作雖然從20世紀70年代已經開始,但因面臨諸多棘手難題而進展緩慢。
為了解決不同剖面間化石物種的保存差異問題,張元動選擇了當時還非常陌生的計算機圖形對比方法,并對這一方法進行了改進。“該方法在國外主要用于油氣勘探領域,在國內還鮮為人知,通過這一方法我們最終成功解決了‘金釘子’界線所要求的高精度劃分對比問題。”張元動說,“此后,這一方法不斷被用到其它‘金釘子’和全球性地質事件的研究中。”
他感嘆道,盡管第一枚“金釘子”的建立過程困難重重,但老一輩科學家的智慧和勇氣,以及對科學的執著追求,往往能峰回路轉,迎來突破。
此后,實驗室研究員金玉玕、陳旭和時任國際地層委員會副主席彭善池等領導的以中國科學家為主的國際工作組,分別為二疊系、奧陶系和寒武系又建立了6枚“金釘子”,使實驗室在國際地層學領域的總體優勢越來越明顯。
2011年7月,位于浙江江山碓邊附近的寒武系江山階“金釘子”確立,成為在我國確立的第十枚“金釘子”,也使我國一躍成為目前世界上擁有“金釘子”最多的國家。
“金釘子”的確立和審批是個嚴謹且漫長的過程。我國加入全球“金釘子”研究比國際同行晚了近20年。現代古生物學和地層學國家重點實驗室“金釘子”研究團隊通過努力,不僅在短時間內實現了趕超,還確立了我國在國際地層學領域的引領地位。
化石是生物演化的最好見證者
隨著多個“金釘子”在我國先后確立,現代古生物學和地層學國家重點實驗室也在國際地層古生物學領域獲得越來越大的話語權。
生物的起源和演化、地球生命系統的演變,化石是最好的見證者。走進現代古生物學和地層學國家重點實驗室,隨便推開一間科研人員的辦公室,最先映入眼簾的無一例外是琳瑯滿目、大大小小的化石。
“化石本身不會告訴你它來自哪個年代,我們實驗室的第一個研究方向——綜合地層,恰恰可以回答這個問題。”現代古生物學和地層學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袁訓來向《中國科學報》介紹了實驗室的5個主要研究方向,分別是綜合地層、早期生命演化、古生代海洋生物演化、陸地生態系統的形成和演化、沉積礦產的基礎地質。
其中,沉積礦產的基礎地質是2019年實驗室優化調整后新納入的研究方向,主要面向國家重大需求和國民經濟主戰場。“除了這個方向,實驗室的另外4個研究方向均處于世界領先地位。”袁訓來以他和朱茂炎領導的早期生命研究團隊為例說,“我們團隊在《自然》《科學》等國際知名期刊上發表的論文,占據該期刊同領域論文數量的20%左右。”
每一項成果的背后都離不開一塊塊化石的發現和研究。2011年夏天的一個晚上,袁訓來接到課題組周傳明打來的電話:“陳哲、王偉、關成國和我在三峽出野外時,從老鄉屋頂廢棄的石堆里發現一塊化石,現在把圖片發你看看。”
收到照片的袁訓來異常驚喜:“這塊看上去有點像芭蕉葉,也有點像烏龜殼的石頭,就是我們一直在尋找的典型的埃迪卡拉生物群化石。”
雖然中國的埃迪卡拉系出露和分布非常廣泛,但在此之前一直沒有發現典型的埃迪卡拉生物群化石。在過去半個多世紀里,全球相同時代地層中發現了30多處埃迪卡拉生物群化石,唯獨在中國沒有。
埃迪卡拉生物群的發現成為我國早期生命研究領域一個重大突破和又一個新的增長點,其中凝聚了幾代科學家的不懈堅持,可謂十年磨一劍,這樣的發現在實驗室發展歷史上還有很多。
當年,現代古生物學和地層學開放研究實驗室研究員陳均遠等人在貴州省甕安地區發現了迄今最古老的動物化石,它們保存在距今6億年前的震旦系含磷地層中,所代表的時代比著名的澄江動物群早了近6000萬年,比澳大利亞埃迪卡拉生物群早2000多萬年。該發現入選1998年度中國基礎科學研究十大新聞。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現代古生物學和地層學國家重點實驗室能取得今天的成績,離不開一代又一代科研人員的執著追求和潛心奉獻。
在南京古生物所工作的侯先光1984年在云南東部的澄江帽天山首次發現澄江動物群化石,隨后,陳均遠、侯先光(云南大學)和舒德干(西北大學)等老一輩科學家通過對澄江動物群化石的不斷挖掘和深入研究,深度詮釋了“寒武紀大爆發”這一令達爾文都感到困惑的重大疑難科學問題,在國際上被譽為“20世紀最驚人的科學發現之一”。該項研究獲得2003年度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
在整個地質歷程中發生了5次生物大滅絕事件,二疊紀末期(2.5 億年前)的生物大滅絕代表顯生宙地球生態系統的最大一次災難,約95%的海洋生物物種和75%的陸地生物物種滅絕。已故中科院院士金玉玕帶領老中青三代科研人員,精細剖析了二疊紀末多門類生物群的演化型式。該項研究也成為金玉玕團隊獲2010年度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最醒目的標志性成果。
地層古生物學是地質學下的二級學科,在全世界范圍內可遴選的地層古生物專業人才非常有限,但從中科院開放實驗室到國家重點實驗室,三代科研人員正將其推向國際舞臺的中心位置。
南京古生物所副所長王軍介紹,實驗室從成立之初,就把培養和穩定人才,特別是優秀中青年人才作為實驗室工作的重點之一。
85后的殷宗軍是現代古生物學和地層學國家重點實驗室最年輕的研究員。他在南京古生物所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在研究員朱茂炎指導下,開展了甕安生物群研究。他在研究過程中發現傳統技術具有明顯的局限性,要取得新的突破,必須引入新技術。隨后,殷宗軍在實驗室和研究所的支持下出國學習同步輻射技術。
“盡管我在國外掌握了同步輻射技術,但儀器設備帶不回來。”回國后的殷宗軍向實驗室和研究所提出申請,希望可以建立高分辨率顯微CT實驗室。2015年,高分辨率顯微CT實驗室最終建成,成為南京古生物所有史以來單體最大、投入最多的實驗室。
“以前聽說過給病人做腦CT,而現在我們可以給化石做CT。”王軍也是高分辨率顯微CT的受益者,其團隊利用該實驗平臺取得了多項科研成果。他贊嘆殷宗軍是“技術小模范”,既會研究,又懂技術,并成功地將技術用于研究工作。
近年來,實驗室開始鼓勵年輕人嘗試應用新技術、開拓新領域,并搭建起實驗室技術平臺。現代古生物學和地層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副主任曹長群負責實驗室技術支撐平臺的建設工作。
“當前,一批新的實驗平臺陸續建成,但我們面臨的最大困難是缺懂技術的人才。”曹長群發現,科學創新既依托于技術手段,又倒逼技術支撐平臺不斷創新實驗技術,使實驗儀器和技術的創新發展有效推動科學研究的創新產出,二者是相輔相成的。
以前有人說,做古生物研究,光學顯微鏡就夠用了,而今地層古生物學領域取得的突破往往離不開技術方法的革新和突破。王軍認為,好的技術人員和好的科研人員相結合,就能做出最好的科研成果。這也是現代古生物學和地層學國家重點實驗室人才培養的方向和目標。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袁訓來希望,未來實驗室的科研人員和技術人員的比例能達到1:1,他鼓勵更多年輕人不僅關注自己的研究領域,還要關注一線技術。
萬紫千紅才是春
來自上古生界研究團隊的研究員王玥每年最期待的就是實驗室的年終總結大會。她說:“實驗室主任的總結報告不僅可以讓我們享受成果大餐,還可以了解實驗室各研究團隊這一年都取得了哪些成果。”
究其原因,還是因為這些成果基本可以代表國內外地層古生物學研究的最新動態和最高水平。王軍告訴記者:“中科院在地層古生物學科特別是古無脊椎動物學領域的大部分研究力量集中在南京古生物所,而南京古生物所90%以上的科研力量又集中在現代古生物學和地層學國家重點實驗室。”
年近90的中科院院士周志炎曾說過,國家給予這么多支持,我們沒有理由不做好自己的學科研究。當年,周志炎是實驗室的核心成員之一,他們那代人腳踏實地、兢兢業業地工作,已經讓我國的地層古生物學研究在國際上占據一席之地。
詹仁斌表示,南京古生物所將舉全所之力建設現代古生物學和地層學國家重點實驗室,為國家培養并維系一支地層古生物學領域的戰略人才隊伍。
談到實驗室有哪些創新的科研組織形式,袁訓來說,我們實驗室每年會拿出300萬元左右的開放基金,面向全國資助30多個地層古生物學領域的研究項目,鼓勵外單位的科研團隊與實驗室的科研人員合作,發揮國家重點實驗室的平臺優勢和作用。
萬紫千紅才是春。現代古生物學和地層學國家重點實驗室不僅用開放基金組織全國的科研力量,還十分重視科學傳播與科教融合工作。
2019年末,一則來自現代古生物學和地層學國家重點實驗室的科研進展新聞在微博的閱讀量達到2.6億次,這讓袁訓來很是意外:“沒想到有這么多人關注我們這個古老又年輕的學科。”同時他也意識到科學傳播的重要性。
現代古生物學和地層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副主任王永棟承擔著研究所科學傳播中心的工作,負責圖書編輯、學術出版、古生物博物館、標本館等方面的科學傳播和普及等任務。他介紹道,科學傳播是研究所的三大中心工作之一,“注重科教融合和科學傳播”已經寫進了實驗室的總體目標。實驗室的多位學科帶頭人均承擔著研究所和實驗室重要學術刊物的主編工作。“這些學術專業出版工作,極大提高了實驗室在國內外地層古生物學界的學術影響力、競爭力和傳播力,其中,《遠古世界》(Palaeoworld)已經成為SCI收錄的國際學術刊物。”
關于科教融合,以現代古生物學和地層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多位學科帶頭人為首的一批“南古人”正在以古生物學為基礎和出發點,與南京大學、北京大學、中國科學院大學、南京信息工程大學等多家高校聯合辦學,講授與古生物學和地層學有關的專業課程、通識課程,普及廣大本科生、研究生的地球生命進化知識。關于科學傳播,南京古生物博物館、化石網和《生物進化》雜志、達爾文大講堂是實驗室對外宣傳的線下線上窗口,博物館每次舉辦的大型公眾科學開放日和全國科普周等系列活動都得到實驗室的大力支持。
如今,在面向國家重大需求和國民經濟主戰場開展應用基礎研究的同時,現代古生物學和地層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利用人才隊伍和實驗技術平臺,正在讓地層古生物學這門小學科在國際舞臺上綻放異彩。
實驗室小故事 把小事做大、做精
“下課的鈴聲響起,戎老師最后一句話也講完了。”
2016年3月,中國科學院院士戎嘉余帶領團隊在南京大學開設“生物演化與環境”通識課。第一次課由戎嘉余親自授課,作為課程負責人的袁訓來在現場發現了這個奇怪的現象。
“50分鐘的課程,第一節課就這樣在鈴聲響起的那一刻結束了,第二節課依然如此。”這個細節讓袁訓來印象深刻,“怎么就那么準呢?”
直到某一天,袁訓來目睹了年逾古稀的院士精心備課的場景后恍然大悟:“哪里有那么巧的事情,這是戎老師精心準備和設計的。這個細節也反映了戎老師做人做事認真的態度。”
認真是成功的前提。2000年,戎嘉余擔任古生物學領域第一個“973”項目的首席科學家,袁訓來記得老師當年寫完項目申請書后就生病住進了醫院,這股認真勁兒也深深感染了他。
“我是該項目第一個子課題的負責人。其他子課題負責人都是研究員,當年我只是副研究員,但老師依然把任務派給了我。”袁訓來回憶道,“最終我帶領團隊順利完成了子課題的任務,獲得了不錯的評價,也在課題結束前評上了研究員。”
“是金子遲早會發光,把小事做大、把小事做精……”如今已經成為實驗室主任的袁訓來不僅記住了老師的話,還付之于實踐,將小門類的化石研究做大、做精,并形成了實驗室獨有的文化氛圍。
在此氛圍中,現代古生物學和地層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始終堅持地層學、門類古生物學的基礎研究,將其作為實驗室的特色和優勢,這也是實驗室各個研究領域的基石和根本。袁訓來解釋道,比如重大生物演化事件研究,地層學和門類古生物學是根本;國家油氣資源勘探和開發,生物地層學是解決產出層位地質時代與精確對比問題的關鍵。
實驗室的文化不是標語和口號,而是深藏人心中、代代相傳的做人做事的信條和準則。實驗室一位年輕人對記者說:“我們年輕人自己不要看輕自己,每個人都力爭在自己的研究領域追求卓越、取得成功,就很了不起了。”
如今的現代古生物學和地層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全體成員在老一輩科學家的影響和號召下,不跟風、不迎合,甘于寂寞、耐得住清貧,努力循著自己的初心,在地層古生物領域,做別人不屑做的、做別人做不了的,求真求實,追求卓越,爭做踐行“三個面向、四個率先”的排頭兵,為國家的資源能源勘探開發、為中國乃至世界地層古生物學事業的發展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現代古生物學和地層學國家重點實驗室簡介
現代古生物學和地層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前身是1989年成立的中國科學院現代古生物學和地層學開放研究實驗室,依托單位是中國科學院南京地質古生物研究所。實驗室在1996年和2000年國家重點和部門開放實驗室評估中,分別列地球科學類第三名和第二名。
2001年7月,經科技部批準,中科院南京地質古生物研究所在原來開放實驗室的基礎上,建設現代古生物學和地層學國家重點實驗室。這是我國唯一專門從事古生物學和地層學研究的國家重點實驗室,主要研究內容是地質歷史時期生命的起源和演化過程及其環境背景等。自2001年升級為國家重點實驗室以來,實驗室在2005、2010和2015年連續3次被評為優秀國家重點實驗室。
實驗室長期致力于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的地層古生物學基礎理論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國際影響的原創科研成果;面向國家重大需求和國民經濟主戰場開展應用基礎研究,快速有效地將地層學最新研究成果應用于我國油氣資源勘探,解決了資源開發中高精度地層劃分和對比等基礎地質難題,在國內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實驗室擁有國際領先的古生物學和地層學實驗技術平臺和大數據平臺,創建的Geobiodiversity Database現已成為國際地層委員會和國際古生物協會的官方數據庫。